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:西山永定河的风土与民俗
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:西山永定河的风土与民俗
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:西山永定河的风土与民俗 《北京文化通志(tōngzhì)·西山永定河卷》 鞠熙 著 北京出版社
《北京文化通志(tōngzhì)·西山永定河卷》 鞠熙 著 北京出版社
 北京西山永定河(yǒngdìnghé)文化带内山灵水秀、人杰地灵,有(yǒu)着非常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与(yǔ)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。但在写作方式上,本书不囿于(yòuyú)文化事项的边界,也不着重(zhuózhòng)介绍某项具体遗产的来龙去脉,而是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,把长时间段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变迁放在它所处的山水环境中(zhōng),着力勾勒大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(xiǎorénwù)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思想史。既有山川自然之风土,亦有社会整体之民俗,简言之,是一次“风俗史”的写作尝试。
第一章“天下之中”讲地理。站在整个东亚大陆来看,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勾勒出地理板块上第二级台阶与(yǔ)东部大平原的交界线,东北到西南一线基本与400毫米等降雨线和胡焕庸线重合,扆山带海,是(shì)海洋交汇大陆的通道。几种不同文明在这里汇通,这使得一个多民族的巨大(jùdà)中国(zhōngguó)(zhōngguó)(zhōngguó)必然会将(jiāng)这里视为“中”点。事实上(shìshíshàng),所有定都北京的政权(zhèngquán),无论其主导者是女真、蒙古、汉人还是满旗,都从未放弃过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,这既是“大中国”得以成立的基础(jīchǔ),也是西山脚下皇家园林的精神追求。从太行山下的小中国,到汇同夷夏的大中国,再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新中国,地理与自然所提供的框架,在西山永定河激荡出千古历史的高歌。
第二章“砺山带河”讲战争(zhànzhēng)。地理格局造成(zàochéng)了文明的冲突与交融,西山永定河正处于这一历史洪流的中(zhōng)心,自然也就承受了更多的激荡和碰撞,甚至是长期惨烈的战争冲突。战争不仅为(wèi)北京造就了幽州骑射、山后八军等历史中的英名,也留下了从长城(chángchéng)脚下到拒马河边大量的战场遗迹。与大房山南簏久为都城不同(bùtóng),自圣水(今大石河)往北,山高险峻、水旱时兴,地无敷土、石多水尽,屯兵戍守和战争移民所带来的大量人口是早期山区开发的主要动力。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底色,这不仅体现在(zài)各种口头传统、民间文艺和生产生活方式中,也体现在性别关系、女性历史乃至当下(dāngxià)节庆仪式(yíshì)之中。
第三章“大禹治水”讲水利。永定河是北京当之无愧的母亲河,也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浑河”“无定河”。北京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,降水季节分配高度不均,全年降水的80%分布在7、8两个月,这造成西山(xīshān)永定河地区的干旱与(yǔ)水灾(shuǐzāi)几乎长年(chángnián)不断。治河为王朝首工,抗旱亦生民常态,遍布(biànbù)各处的龙王庙正是这种人-水关系(guānxì)的具象表达。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龙王爷以及千奇百怪的龙王故事,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与水的多样关系,以及为了适应这种人-水关系所形成(xíngchéng)的社会结构(jiégòu)与集体精神(jīngshén)。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,西山永定河地区不算那么(nàme)优越的水文条件,在考验人类意志与智慧的同时,也教会了人们团结、协作与勇气。
第四章(dìsìzhāng)“耕樵栗园”讲耕作。西山如皇居之右胁(zhīyòuxié)延展而南,“磅礴数千里,林麓苍黝,溪涧镂错,其中(qízhōng)物产(wùchǎn)甚饶,古称神皋隩区也”。千百年来普通民众在山河之间耕种(gēngzhòng)蕃育,才创造出今日所见的(de)丰富(fēngfù)物产与多样景观。西山之中、永定河畔,我们最早能找到的农作物是粟黍,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,东胡林人很(hěn)可能已经开始在清水河畔耕种粟黍,并由此形成一种半定居的生活方式。至今西山永定河区域内仍主要以粟、黍、高粱、玉米等旱作作物为主要种植对象,只在海淀、胡良河上游、昌平白浮泉这些泉水丰盈、地热资源丰富的地方有水稻种植。在更(gèng)难开发的高山上,枣栗成为主要作物。而帝京繁华都(dōu)会,也在近郊膏腴(gāoyú)之处催生出精巧的莳花弄蔬技艺。多样的耕作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产,也渲染出山河之中民俗文化的主色调。
第五章“白石乌金”讲矿产。中国以农为(wèi)本,但西山少有良田,反而是“五代同堂”的地(dì)层构造,为居住(jūzhù)于(yú)此的人民备好了地底的馈赠。北京很早就以美玉(měiyù)“燕石”而闻名,房山汉白玉历来(lìlái)是皇室宫殿的御用品。辽代以后,官办采石地集中(jízhōng)在大石窝,围绕白石的生产运输所形成的小社会,直到21世纪初封山令后方戛然而止。另一种帝王御用的矿业制品是琉璃,至少从元代开始,琉璃渠村已有官办琉璃窑。这种原本来自西域的建材,在西山永定河海纳百川(hǎinàbǎichuān)的气度中,最终被凝练成中国民族建筑的显著标志。与(yǔ)帝王气度的燕石、琉璃相比,煤炭则更贴近于普通人生活的满面尘灰烟火色。
第六章“洞天(dòngtiān)福地”讲灵气。西山之内(nèi)有多处洞天福地,它们不仅历来被认为是(shì)灵气汇聚之所,也是帝王求雨、寻仙访道(fǎngdào)和采药炼丹的(de)(de)(de)仙境(xiānjìng)。燕齐地区是道教信仰的发源地,北京西山一带也位于早期神仙(shénxiān)信仰的核心区域内。尤其是大房山,很早就被视为(shìwèi)神仙往来居住的避世仙境。一代又一代的隐者道士入山修行,这并非只是文学想象,而是战火灾祸延绵(yánmián)纷扰的时代中人们常见的选择。那峰峦叠嶂的西山群山,和平时可能是阻绝交通的屏障,乱世中反而是避祸的桃花源。也许是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品格使然,避世之人采药、讲学、著书、访仙,遨游于天地山川之间,却往往兼具心系天下众生的责任感。孔水洞内刻经雕像、白带山上石室藏经、遍访洞天为民祈雨,历代(lìdài)进山访道的人们,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了超越性的文化品格,同时也借神仙之名,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自然与文化的宝贵遗产。
第七章“西方乐土”讲(jiǎng)宗教。西山多寺,历来为文人所称道,其中又尤以佛寺为最。汉末时佛教僧人开始进入京西山区,他们中有些接管了汉末世家大族留下的(de)基业,有的则开始在(zài)山中(shānzhōng)勉力经营,到隋唐时期僧人已对当地社会(shèhuì)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。佛寺结千人之社、聚千人之心,成为地方社会和皇权(huángquán)之间的中介,这在唐代幽州已见端倪(duānní),也为以后历代佛教发展绘制了背景。辽金(liáojīn)时期,佛寺逐渐成为山区村落社会的中心。除此之外,来自草原的政权也借助佛教的世界性,构建起跨区域、跨民族、跨国界的庞大网络。
第八章“社邑香会”讲庙会。庙会在寺庙(sìmiào)中进行,但大多无关僧道,千百万普通民众才是主角(zhǔjué)。如果我们将发生在寺庙中的群体性、年度性节庆仪式都视为庙会的话,那么西山永定河(yǒngdìnghé)地区的各类庙会常常与社会组织规模有关,根据其层级关系可以分为三种:单村之会、联村走会与众村朝山。而妙峰山,则(zé)是由北京市民、商人、学者(xuézhě)们层垒而成的金顶(jīndǐng)。
第九章“万千生灵”讲自然。北京既是多样文明交融发展的典范,也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,万千生灵与千万(qiānwàn)人民一起,在山河(shānhé)大地上历经漫长岁月而生生不息。这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(jiāoxiānghuīyìng)的状态,当然首先得益于山河互构(hùgòu)所形成的多样性地理环境,但长期以来北京作为王朝国家的都城,中华文明以灵台(língtái)囿沼和鱼藻之乐为最高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,也是造成生态平衡(shēngtàipínghéng)与环境友好的重要原因。
作为一以贯之的主旨,本书的写作立场可以用(yòng)以下八个字来概括(gàikuò):山河永固,人民万岁。
(作者为(wèi)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)
北京西山永定河(yǒngdìnghé)文化带内山灵水秀、人杰地灵,有(yǒu)着非常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与(yǔ)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。但在写作方式上,本书不囿于(yòuyú)文化事项的边界,也不着重(zhuózhòng)介绍某项具体遗产的来龙去脉,而是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,把长时间段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变迁放在它所处的山水环境中(zhōng),着力勾勒大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(xiǎorénwù)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思想史。既有山川自然之风土,亦有社会整体之民俗,简言之,是一次“风俗史”的写作尝试。
第一章“天下之中”讲地理。站在整个东亚大陆来看,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勾勒出地理板块上第二级台阶与(yǔ)东部大平原的交界线,东北到西南一线基本与400毫米等降雨线和胡焕庸线重合,扆山带海,是(shì)海洋交汇大陆的通道。几种不同文明在这里汇通,这使得一个多民族的巨大(jùdà)中国(zhōngguó)(zhōngguó)(zhōngguó)必然会将(jiāng)这里视为“中”点。事实上(shìshíshàng),所有定都北京的政权(zhèngquán),无论其主导者是女真、蒙古、汉人还是满旗,都从未放弃过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,这既是“大中国”得以成立的基础(jīchǔ),也是西山脚下皇家园林的精神追求。从太行山下的小中国,到汇同夷夏的大中国,再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新中国,地理与自然所提供的框架,在西山永定河激荡出千古历史的高歌。
第二章“砺山带河”讲战争(zhànzhēng)。地理格局造成(zàochéng)了文明的冲突与交融,西山永定河正处于这一历史洪流的中(zhōng)心,自然也就承受了更多的激荡和碰撞,甚至是长期惨烈的战争冲突。战争不仅为(wèi)北京造就了幽州骑射、山后八军等历史中的英名,也留下了从长城(chángchéng)脚下到拒马河边大量的战场遗迹。与大房山南簏久为都城不同(bùtóng),自圣水(今大石河)往北,山高险峻、水旱时兴,地无敷土、石多水尽,屯兵戍守和战争移民所带来的大量人口是早期山区开发的主要动力。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底色,这不仅体现在(zài)各种口头传统、民间文艺和生产生活方式中,也体现在性别关系、女性历史乃至当下(dāngxià)节庆仪式(yíshì)之中。
第三章“大禹治水”讲水利。永定河是北京当之无愧的母亲河,也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浑河”“无定河”。北京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,降水季节分配高度不均,全年降水的80%分布在7、8两个月,这造成西山(xīshān)永定河地区的干旱与(yǔ)水灾(shuǐzāi)几乎长年(chángnián)不断。治河为王朝首工,抗旱亦生民常态,遍布(biànbù)各处的龙王庙正是这种人-水关系(guānxì)的具象表达。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龙王爷以及千奇百怪的龙王故事,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与水的多样关系,以及为了适应这种人-水关系所形成(xíngchéng)的社会结构(jiégòu)与集体精神(jīngshén)。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,西山永定河地区不算那么(nàme)优越的水文条件,在考验人类意志与智慧的同时,也教会了人们团结、协作与勇气。
第四章(dìsìzhāng)“耕樵栗园”讲耕作。西山如皇居之右胁(zhīyòuxié)延展而南,“磅礴数千里,林麓苍黝,溪涧镂错,其中(qízhōng)物产(wùchǎn)甚饶,古称神皋隩区也”。千百年来普通民众在山河之间耕种(gēngzhòng)蕃育,才创造出今日所见的(de)丰富(fēngfù)物产与多样景观。西山之中、永定河畔,我们最早能找到的农作物是粟黍,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,东胡林人很(hěn)可能已经开始在清水河畔耕种粟黍,并由此形成一种半定居的生活方式。至今西山永定河区域内仍主要以粟、黍、高粱、玉米等旱作作物为主要种植对象,只在海淀、胡良河上游、昌平白浮泉这些泉水丰盈、地热资源丰富的地方有水稻种植。在更(gèng)难开发的高山上,枣栗成为主要作物。而帝京繁华都(dōu)会,也在近郊膏腴(gāoyú)之处催生出精巧的莳花弄蔬技艺。多样的耕作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产,也渲染出山河之中民俗文化的主色调。
第五章“白石乌金”讲矿产。中国以农为(wèi)本,但西山少有良田,反而是“五代同堂”的地(dì)层构造,为居住(jūzhù)于(yú)此的人民备好了地底的馈赠。北京很早就以美玉(měiyù)“燕石”而闻名,房山汉白玉历来(lìlái)是皇室宫殿的御用品。辽代以后,官办采石地集中(jízhōng)在大石窝,围绕白石的生产运输所形成的小社会,直到21世纪初封山令后方戛然而止。另一种帝王御用的矿业制品是琉璃,至少从元代开始,琉璃渠村已有官办琉璃窑。这种原本来自西域的建材,在西山永定河海纳百川(hǎinàbǎichuān)的气度中,最终被凝练成中国民族建筑的显著标志。与(yǔ)帝王气度的燕石、琉璃相比,煤炭则更贴近于普通人生活的满面尘灰烟火色。
第六章“洞天(dòngtiān)福地”讲灵气。西山之内(nèi)有多处洞天福地,它们不仅历来被认为是(shì)灵气汇聚之所,也是帝王求雨、寻仙访道(fǎngdào)和采药炼丹的(de)(de)(de)仙境(xiānjìng)。燕齐地区是道教信仰的发源地,北京西山一带也位于早期神仙(shénxiān)信仰的核心区域内。尤其是大房山,很早就被视为(shìwèi)神仙往来居住的避世仙境。一代又一代的隐者道士入山修行,这并非只是文学想象,而是战火灾祸延绵(yánmián)纷扰的时代中人们常见的选择。那峰峦叠嶂的西山群山,和平时可能是阻绝交通的屏障,乱世中反而是避祸的桃花源。也许是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品格使然,避世之人采药、讲学、著书、访仙,遨游于天地山川之间,却往往兼具心系天下众生的责任感。孔水洞内刻经雕像、白带山上石室藏经、遍访洞天为民祈雨,历代(lìdài)进山访道的人们,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了超越性的文化品格,同时也借神仙之名,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自然与文化的宝贵遗产。
第七章“西方乐土”讲(jiǎng)宗教。西山多寺,历来为文人所称道,其中又尤以佛寺为最。汉末时佛教僧人开始进入京西山区,他们中有些接管了汉末世家大族留下的(de)基业,有的则开始在(zài)山中(shānzhōng)勉力经营,到隋唐时期僧人已对当地社会(shèhuì)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。佛寺结千人之社、聚千人之心,成为地方社会和皇权(huángquán)之间的中介,这在唐代幽州已见端倪(duānní),也为以后历代佛教发展绘制了背景。辽金(liáojīn)时期,佛寺逐渐成为山区村落社会的中心。除此之外,来自草原的政权也借助佛教的世界性,构建起跨区域、跨民族、跨国界的庞大网络。
第八章“社邑香会”讲庙会。庙会在寺庙(sìmiào)中进行,但大多无关僧道,千百万普通民众才是主角(zhǔjué)。如果我们将发生在寺庙中的群体性、年度性节庆仪式都视为庙会的话,那么西山永定河(yǒngdìnghé)地区的各类庙会常常与社会组织规模有关,根据其层级关系可以分为三种:单村之会、联村走会与众村朝山。而妙峰山,则(zé)是由北京市民、商人、学者(xuézhě)们层垒而成的金顶(jīndǐng)。
第九章“万千生灵”讲自然。北京既是多样文明交融发展的典范,也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,万千生灵与千万(qiānwàn)人民一起,在山河(shānhé)大地上历经漫长岁月而生生不息。这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(jiāoxiānghuīyìng)的状态,当然首先得益于山河互构(hùgòu)所形成的多样性地理环境,但长期以来北京作为王朝国家的都城,中华文明以灵台(língtái)囿沼和鱼藻之乐为最高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,也是造成生态平衡(shēngtàipínghéng)与环境友好的重要原因。
作为一以贯之的主旨,本书的写作立场可以用(yòng)以下八个字来概括(gàikuò):山河永固,人民万岁。
(作者为(wèi)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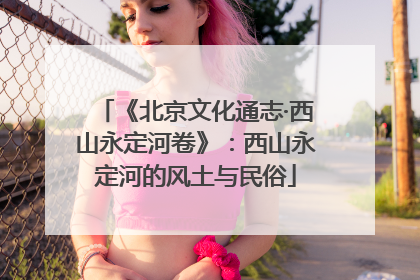
 《北京文化通志(tōngzhì)·西山永定河卷》 鞠熙 著 北京出版社
《北京文化通志(tōngzhì)·西山永定河卷》 鞠熙 著 北京出版社
 北京西山永定河(yǒngdìnghé)文化带内山灵水秀、人杰地灵,有(yǒu)着非常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与(yǔ)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。但在写作方式上,本书不囿于(yòuyú)文化事项的边界,也不着重(zhuózhòng)介绍某项具体遗产的来龙去脉,而是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,把长时间段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变迁放在它所处的山水环境中(zhōng),着力勾勒大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(xiǎorénwù)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思想史。既有山川自然之风土,亦有社会整体之民俗,简言之,是一次“风俗史”的写作尝试。
第一章“天下之中”讲地理。站在整个东亚大陆来看,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勾勒出地理板块上第二级台阶与(yǔ)东部大平原的交界线,东北到西南一线基本与400毫米等降雨线和胡焕庸线重合,扆山带海,是(shì)海洋交汇大陆的通道。几种不同文明在这里汇通,这使得一个多民族的巨大(jùdà)中国(zhōngguó)(zhōngguó)(zhōngguó)必然会将(jiāng)这里视为“中”点。事实上(shìshíshàng),所有定都北京的政权(zhèngquán),无论其主导者是女真、蒙古、汉人还是满旗,都从未放弃过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,这既是“大中国”得以成立的基础(jīchǔ),也是西山脚下皇家园林的精神追求。从太行山下的小中国,到汇同夷夏的大中国,再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新中国,地理与自然所提供的框架,在西山永定河激荡出千古历史的高歌。
第二章“砺山带河”讲战争(zhànzhēng)。地理格局造成(zàochéng)了文明的冲突与交融,西山永定河正处于这一历史洪流的中(zhōng)心,自然也就承受了更多的激荡和碰撞,甚至是长期惨烈的战争冲突。战争不仅为(wèi)北京造就了幽州骑射、山后八军等历史中的英名,也留下了从长城(chángchéng)脚下到拒马河边大量的战场遗迹。与大房山南簏久为都城不同(bùtóng),自圣水(今大石河)往北,山高险峻、水旱时兴,地无敷土、石多水尽,屯兵戍守和战争移民所带来的大量人口是早期山区开发的主要动力。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底色,这不仅体现在(zài)各种口头传统、民间文艺和生产生活方式中,也体现在性别关系、女性历史乃至当下(dāngxià)节庆仪式(yíshì)之中。
第三章“大禹治水”讲水利。永定河是北京当之无愧的母亲河,也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浑河”“无定河”。北京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,降水季节分配高度不均,全年降水的80%分布在7、8两个月,这造成西山(xīshān)永定河地区的干旱与(yǔ)水灾(shuǐzāi)几乎长年(chángnián)不断。治河为王朝首工,抗旱亦生民常态,遍布(biànbù)各处的龙王庙正是这种人-水关系(guānxì)的具象表达。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龙王爷以及千奇百怪的龙王故事,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与水的多样关系,以及为了适应这种人-水关系所形成(xíngchéng)的社会结构(jiégòu)与集体精神(jīngshén)。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,西山永定河地区不算那么(nàme)优越的水文条件,在考验人类意志与智慧的同时,也教会了人们团结、协作与勇气。
第四章(dìsìzhāng)“耕樵栗园”讲耕作。西山如皇居之右胁(zhīyòuxié)延展而南,“磅礴数千里,林麓苍黝,溪涧镂错,其中(qízhōng)物产(wùchǎn)甚饶,古称神皋隩区也”。千百年来普通民众在山河之间耕种(gēngzhòng)蕃育,才创造出今日所见的(de)丰富(fēngfù)物产与多样景观。西山之中、永定河畔,我们最早能找到的农作物是粟黍,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,东胡林人很(hěn)可能已经开始在清水河畔耕种粟黍,并由此形成一种半定居的生活方式。至今西山永定河区域内仍主要以粟、黍、高粱、玉米等旱作作物为主要种植对象,只在海淀、胡良河上游、昌平白浮泉这些泉水丰盈、地热资源丰富的地方有水稻种植。在更(gèng)难开发的高山上,枣栗成为主要作物。而帝京繁华都(dōu)会,也在近郊膏腴(gāoyú)之处催生出精巧的莳花弄蔬技艺。多样的耕作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产,也渲染出山河之中民俗文化的主色调。
第五章“白石乌金”讲矿产。中国以农为(wèi)本,但西山少有良田,反而是“五代同堂”的地(dì)层构造,为居住(jūzhù)于(yú)此的人民备好了地底的馈赠。北京很早就以美玉(měiyù)“燕石”而闻名,房山汉白玉历来(lìlái)是皇室宫殿的御用品。辽代以后,官办采石地集中(jízhōng)在大石窝,围绕白石的生产运输所形成的小社会,直到21世纪初封山令后方戛然而止。另一种帝王御用的矿业制品是琉璃,至少从元代开始,琉璃渠村已有官办琉璃窑。这种原本来自西域的建材,在西山永定河海纳百川(hǎinàbǎichuān)的气度中,最终被凝练成中国民族建筑的显著标志。与(yǔ)帝王气度的燕石、琉璃相比,煤炭则更贴近于普通人生活的满面尘灰烟火色。
第六章“洞天(dòngtiān)福地”讲灵气。西山之内(nèi)有多处洞天福地,它们不仅历来被认为是(shì)灵气汇聚之所,也是帝王求雨、寻仙访道(fǎngdào)和采药炼丹的(de)(de)(de)仙境(xiānjìng)。燕齐地区是道教信仰的发源地,北京西山一带也位于早期神仙(shénxiān)信仰的核心区域内。尤其是大房山,很早就被视为(shìwèi)神仙往来居住的避世仙境。一代又一代的隐者道士入山修行,这并非只是文学想象,而是战火灾祸延绵(yánmián)纷扰的时代中人们常见的选择。那峰峦叠嶂的西山群山,和平时可能是阻绝交通的屏障,乱世中反而是避祸的桃花源。也许是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品格使然,避世之人采药、讲学、著书、访仙,遨游于天地山川之间,却往往兼具心系天下众生的责任感。孔水洞内刻经雕像、白带山上石室藏经、遍访洞天为民祈雨,历代(lìdài)进山访道的人们,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了超越性的文化品格,同时也借神仙之名,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自然与文化的宝贵遗产。
第七章“西方乐土”讲(jiǎng)宗教。西山多寺,历来为文人所称道,其中又尤以佛寺为最。汉末时佛教僧人开始进入京西山区,他们中有些接管了汉末世家大族留下的(de)基业,有的则开始在(zài)山中(shānzhōng)勉力经营,到隋唐时期僧人已对当地社会(shèhuì)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。佛寺结千人之社、聚千人之心,成为地方社会和皇权(huángquán)之间的中介,这在唐代幽州已见端倪(duānní),也为以后历代佛教发展绘制了背景。辽金(liáojīn)时期,佛寺逐渐成为山区村落社会的中心。除此之外,来自草原的政权也借助佛教的世界性,构建起跨区域、跨民族、跨国界的庞大网络。
第八章“社邑香会”讲庙会。庙会在寺庙(sìmiào)中进行,但大多无关僧道,千百万普通民众才是主角(zhǔjué)。如果我们将发生在寺庙中的群体性、年度性节庆仪式都视为庙会的话,那么西山永定河(yǒngdìnghé)地区的各类庙会常常与社会组织规模有关,根据其层级关系可以分为三种:单村之会、联村走会与众村朝山。而妙峰山,则(zé)是由北京市民、商人、学者(xuézhě)们层垒而成的金顶(jīndǐng)。
第九章“万千生灵”讲自然。北京既是多样文明交融发展的典范,也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,万千生灵与千万(qiānwàn)人民一起,在山河(shānhé)大地上历经漫长岁月而生生不息。这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(jiāoxiānghuīyìng)的状态,当然首先得益于山河互构(hùgòu)所形成的多样性地理环境,但长期以来北京作为王朝国家的都城,中华文明以灵台(língtái)囿沼和鱼藻之乐为最高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,也是造成生态平衡(shēngtàipínghéng)与环境友好的重要原因。
作为一以贯之的主旨,本书的写作立场可以用(yòng)以下八个字来概括(gàikuò):山河永固,人民万岁。
(作者为(wèi)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)
北京西山永定河(yǒngdìnghé)文化带内山灵水秀、人杰地灵,有(yǒu)着非常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与(yǔ)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。但在写作方式上,本书不囿于(yòuyú)文化事项的边界,也不着重(zhuózhòng)介绍某项具体遗产的来龙去脉,而是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,把长时间段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变迁放在它所处的山水环境中(zhōng),着力勾勒大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(xiǎorénwù)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思想史。既有山川自然之风土,亦有社会整体之民俗,简言之,是一次“风俗史”的写作尝试。
第一章“天下之中”讲地理。站在整个东亚大陆来看,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勾勒出地理板块上第二级台阶与(yǔ)东部大平原的交界线,东北到西南一线基本与400毫米等降雨线和胡焕庸线重合,扆山带海,是(shì)海洋交汇大陆的通道。几种不同文明在这里汇通,这使得一个多民族的巨大(jùdà)中国(zhōngguó)(zhōngguó)(zhōngguó)必然会将(jiāng)这里视为“中”点。事实上(shìshíshàng),所有定都北京的政权(zhèngquán),无论其主导者是女真、蒙古、汉人还是满旗,都从未放弃过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,这既是“大中国”得以成立的基础(jīchǔ),也是西山脚下皇家园林的精神追求。从太行山下的小中国,到汇同夷夏的大中国,再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新中国,地理与自然所提供的框架,在西山永定河激荡出千古历史的高歌。
第二章“砺山带河”讲战争(zhànzhēng)。地理格局造成(zàochéng)了文明的冲突与交融,西山永定河正处于这一历史洪流的中(zhōng)心,自然也就承受了更多的激荡和碰撞,甚至是长期惨烈的战争冲突。战争不仅为(wèi)北京造就了幽州骑射、山后八军等历史中的英名,也留下了从长城(chángchéng)脚下到拒马河边大量的战场遗迹。与大房山南簏久为都城不同(bùtóng),自圣水(今大石河)往北,山高险峻、水旱时兴,地无敷土、石多水尽,屯兵戍守和战争移民所带来的大量人口是早期山区开发的主要动力。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底色,这不仅体现在(zài)各种口头传统、民间文艺和生产生活方式中,也体现在性别关系、女性历史乃至当下(dāngxià)节庆仪式(yíshì)之中。
第三章“大禹治水”讲水利。永定河是北京当之无愧的母亲河,也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浑河”“无定河”。北京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,降水季节分配高度不均,全年降水的80%分布在7、8两个月,这造成西山(xīshān)永定河地区的干旱与(yǔ)水灾(shuǐzāi)几乎长年(chángnián)不断。治河为王朝首工,抗旱亦生民常态,遍布(biànbù)各处的龙王庙正是这种人-水关系(guānxì)的具象表达。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龙王爷以及千奇百怪的龙王故事,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与水的多样关系,以及为了适应这种人-水关系所形成(xíngchéng)的社会结构(jiégòu)与集体精神(jīngshén)。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,西山永定河地区不算那么(nàme)优越的水文条件,在考验人类意志与智慧的同时,也教会了人们团结、协作与勇气。
第四章(dìsìzhāng)“耕樵栗园”讲耕作。西山如皇居之右胁(zhīyòuxié)延展而南,“磅礴数千里,林麓苍黝,溪涧镂错,其中(qízhōng)物产(wùchǎn)甚饶,古称神皋隩区也”。千百年来普通民众在山河之间耕种(gēngzhòng)蕃育,才创造出今日所见的(de)丰富(fēngfù)物产与多样景观。西山之中、永定河畔,我们最早能找到的农作物是粟黍,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,东胡林人很(hěn)可能已经开始在清水河畔耕种粟黍,并由此形成一种半定居的生活方式。至今西山永定河区域内仍主要以粟、黍、高粱、玉米等旱作作物为主要种植对象,只在海淀、胡良河上游、昌平白浮泉这些泉水丰盈、地热资源丰富的地方有水稻种植。在更(gèng)难开发的高山上,枣栗成为主要作物。而帝京繁华都(dōu)会,也在近郊膏腴(gāoyú)之处催生出精巧的莳花弄蔬技艺。多样的耕作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产,也渲染出山河之中民俗文化的主色调。
第五章“白石乌金”讲矿产。中国以农为(wèi)本,但西山少有良田,反而是“五代同堂”的地(dì)层构造,为居住(jūzhù)于(yú)此的人民备好了地底的馈赠。北京很早就以美玉(měiyù)“燕石”而闻名,房山汉白玉历来(lìlái)是皇室宫殿的御用品。辽代以后,官办采石地集中(jízhōng)在大石窝,围绕白石的生产运输所形成的小社会,直到21世纪初封山令后方戛然而止。另一种帝王御用的矿业制品是琉璃,至少从元代开始,琉璃渠村已有官办琉璃窑。这种原本来自西域的建材,在西山永定河海纳百川(hǎinàbǎichuān)的气度中,最终被凝练成中国民族建筑的显著标志。与(yǔ)帝王气度的燕石、琉璃相比,煤炭则更贴近于普通人生活的满面尘灰烟火色。
第六章“洞天(dòngtiān)福地”讲灵气。西山之内(nèi)有多处洞天福地,它们不仅历来被认为是(shì)灵气汇聚之所,也是帝王求雨、寻仙访道(fǎngdào)和采药炼丹的(de)(de)(de)仙境(xiānjìng)。燕齐地区是道教信仰的发源地,北京西山一带也位于早期神仙(shénxiān)信仰的核心区域内。尤其是大房山,很早就被视为(shìwèi)神仙往来居住的避世仙境。一代又一代的隐者道士入山修行,这并非只是文学想象,而是战火灾祸延绵(yánmián)纷扰的时代中人们常见的选择。那峰峦叠嶂的西山群山,和平时可能是阻绝交通的屏障,乱世中反而是避祸的桃花源。也许是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品格使然,避世之人采药、讲学、著书、访仙,遨游于天地山川之间,却往往兼具心系天下众生的责任感。孔水洞内刻经雕像、白带山上石室藏经、遍访洞天为民祈雨,历代(lìdài)进山访道的人们,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了超越性的文化品格,同时也借神仙之名,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自然与文化的宝贵遗产。
第七章“西方乐土”讲(jiǎng)宗教。西山多寺,历来为文人所称道,其中又尤以佛寺为最。汉末时佛教僧人开始进入京西山区,他们中有些接管了汉末世家大族留下的(de)基业,有的则开始在(zài)山中(shānzhōng)勉力经营,到隋唐时期僧人已对当地社会(shèhuì)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。佛寺结千人之社、聚千人之心,成为地方社会和皇权(huángquán)之间的中介,这在唐代幽州已见端倪(duānní),也为以后历代佛教发展绘制了背景。辽金(liáojīn)时期,佛寺逐渐成为山区村落社会的中心。除此之外,来自草原的政权也借助佛教的世界性,构建起跨区域、跨民族、跨国界的庞大网络。
第八章“社邑香会”讲庙会。庙会在寺庙(sìmiào)中进行,但大多无关僧道,千百万普通民众才是主角(zhǔjué)。如果我们将发生在寺庙中的群体性、年度性节庆仪式都视为庙会的话,那么西山永定河(yǒngdìnghé)地区的各类庙会常常与社会组织规模有关,根据其层级关系可以分为三种:单村之会、联村走会与众村朝山。而妙峰山,则(zé)是由北京市民、商人、学者(xuézhě)们层垒而成的金顶(jīndǐng)。
第九章“万千生灵”讲自然。北京既是多样文明交融发展的典范,也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,万千生灵与千万(qiānwàn)人民一起,在山河(shānhé)大地上历经漫长岁月而生生不息。这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(jiāoxiānghuīyìng)的状态,当然首先得益于山河互构(hùgòu)所形成的多样性地理环境,但长期以来北京作为王朝国家的都城,中华文明以灵台(língtái)囿沼和鱼藻之乐为最高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,也是造成生态平衡(shēngtàipínghéng)与环境友好的重要原因。
作为一以贯之的主旨,本书的写作立场可以用(yòng)以下八个字来概括(gàikuò):山河永固,人民万岁。
(作者为(wèi)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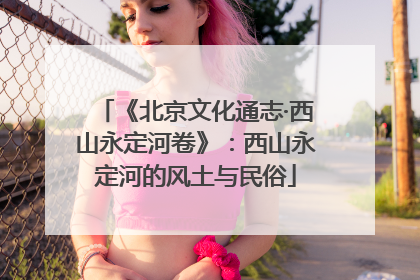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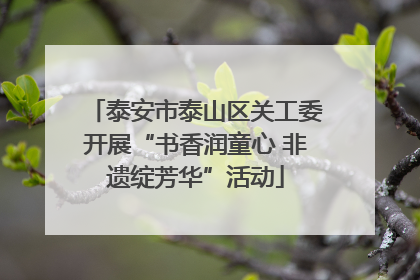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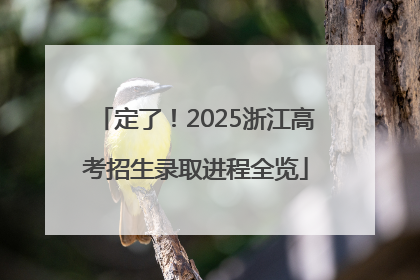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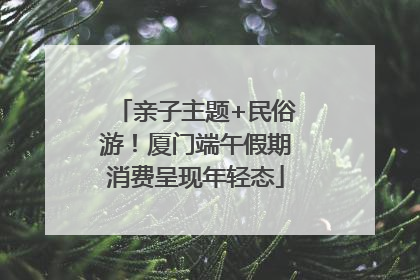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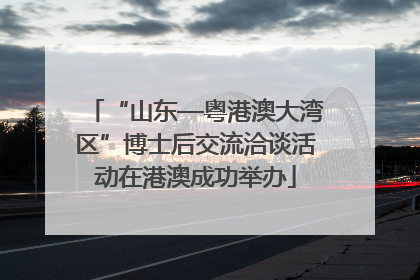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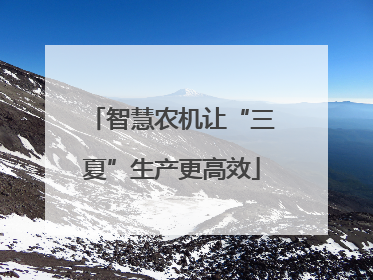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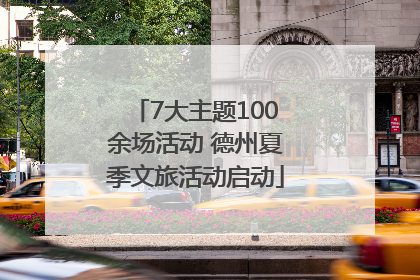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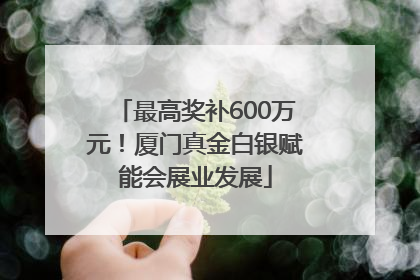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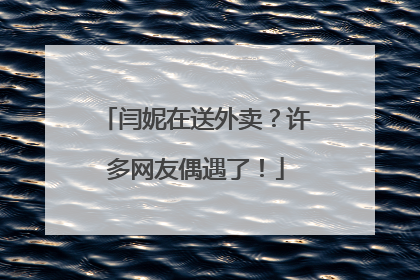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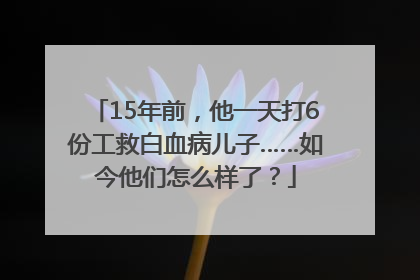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